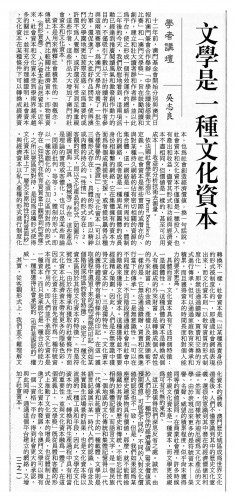吳志良
十二年前,澳門基金會開始分別與澳門日報和澳門筆會合作舉辦「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和「澳門文學獎」,旨在鼓勵閱讀和創作,建立和壯大讀者群和作者群,並以此為平台,使之形成一個有效運作的網絡。十二年後的今天,我們欣慰地看到,這兩項活動已經達到推廣閱讀風氣和激發創作動力的目的,不僅吸引了數以千計的讀者和作者參與這兩項賽事,為澳門文學界培養了一批生力軍,還促進了一大批好作品問世,使得澳門的文學園地更加蔥翠茂盛。至為重要的或許還不為人覺察,或許還沒有受到足夠重視,這些作者、這些作品大大增加了澳門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
資本是用來解釋社會積累性的一個概念。傳統上,人們比較關注經濟資本,即物質資本(有形資產)、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近年來,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並有充分的理據證明,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在某種條件下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也為社會創造經濟價值。換一句話說,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不僅僅是一種投入,也有產出和收益,儘管其形式和功能與經濟資本不盡相同,但價值是一樣的,甚至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技術去測量。
依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定義,「社會資本是那些實際的或潛在的、與對某種持久網絡的佔有密切相關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一網絡是一種眾所周知的、體制化的網絡,或者說是一種與某個團體的成員身份相聯繫的網絡,它在集體擁有的資本方面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援,或者提供贏得各種各樣聲譽的『憑證』」;而文化資本「可以以三種形式存在:1、具體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體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2、客觀的形式,即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如圖片、圖書、詞典、工具、機械等)存在,這些產品是理論的實現或客體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論,問題的批判,等等;3、體制的形式,即以一種客觀化的、必須加以區別對待的形式存在(如我們在教育資質當中觀察到的那樣),之所以要區別對待,是因為這種形式使得文化資本披上了一層完全原始性的財富面紗」。與經濟資本以私人產權的形式進行制度化轉換不一樣,社會資本是「以某種高貴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即通過社會網絡表現出來;而文化資本則「以教育資質的形式制度化」即無法通過饋贈、買賣和交換的方式進行傳承,但可以通過家庭教育來傳承和積累,而且獲得資本的時間長度和對個人能力的要求更高。
具體而言,文化資本具有下述四個特徵:一是個體性。「這種具體的資本是轉換成個人有機組成的外來財富,是轉換成個人習性的外來財富,和金錢、產權以及貴族頭銜不一樣的是,它無法通過饋贈、買賣、和交換進行當下的傳承」。二是無意識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階段裡通過社會和社會中的階級來獲得文化資本。這種獲得並不需要經過精心策劃,因此,人們是在無意識中獲得文化資本的」。三是獨特性。「文化資本的獲得總是帶有最初條件的印記,在這一獲取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或明或隱的印記(例如某個階段或地區的發音特徵),決定了一種文化資本區別於其他文化資本的特徵」。四是符號性。「由於在傳承和獲取的社會條件方面,文化資本比經濟資本帶有更多的隱秘色彩,因此,文化資本往往首先是作為一種符號資本而起作用的,即人們並不承認文化資本是一種資本。而只是承認它是一種合法的能力、一種能獲得社會承認的(也許是誤認的)權威」。
其實,從客觀形式上,我們並不難理解文化資本的涵義。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人們不僅意識到其中的歷史文化意義,還很快意識到其中潛在的經濟價值和利益。然而,同樣被布迪厄視為文化產品的文學,由於表現出來更多的是符號資本——榮譽、名聲、威望的積累程度,似乎尚未獲得同等的價值認同。在商業社會裡,許多時候並不視文化資本是一種資本,而文學更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這正是值得我們深思反省之處。誠然,由於人們給予一種物品的經濟價值(需求價值或預期價值)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對文化價值的認定也不一致,但是,我們如果認為某座歷史建築物具有價值,那麼,就不能割捨隱藏於其背後的歷史和傳統,不能忘記世代相傳的集體記憶。而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文化傳統和集體記憶得以一代一代傳承和延續下去的一種載體,文學則是語言記錄展示某一時代人們的認識、信念及其實踐生活場景的結果,也是文化資本得以流通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因此,文學在文化資本的生成、轉換和再生產過程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並與文化資本融為一體了。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獎」既從具體和客觀的形式上推動了文化資本的增長,也從體制上促進了文化資本的發展,令澳門文學可以擁有一個「資格」平台,得到社會更大的承認。與此同時,通過這個平台建立的網絡,又增加了社會資本。
(二之一)